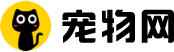周明全批评要去职业化而变为生活化
更新时间:2020-05-09 14:20:51
周明全
蔡丽,女,汉族,1976年出生于四川。在西南师范大学获本科,硕士,在苏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6年7月起执教于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云南文学的研究、批评。出版学术著作《鲁迅研究的四维审视》(合著),专著《传统 、政治与文学》,在《当代作家评论》、《甘肃社会科学》、《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
主持人语:
一次,当我谈起蔡丽近期写雷平阳的评论文章很棒时,同桌一位朋友马上插话,很严肃地说,蔡丽可是个真博士。这乍听起来很滑稽,却道出了蔡丽作为批评家学养上的深厚 在假博士横行的时代,一个真字,是对一位寒窗数十余载的、有才情的博士最大的肯定。
蔡丽原籍四川,有着四川人泼辣的一面,做事风风火火,虽然远嫁云南,但未被温吞的云南慢性格同化,这用批评的行话来说是批评家的主体性很强大。彩丽的批评呈现出感性直觉和理论阐释很好地结合的风貌,这和她真博士的学养和性情中人也是相得益彰的。
蔡丽早年是做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但让我甚为佩服的是,她的批评观却很中正,这是我愿意与之交往的主要原因 我本人对过左的文学观是讨厌的。近年来,她主要精力花费在云南诗歌的研究上,撰写了包括于坚、海男、雷平阳等在内的多位诗人的研究文章,很好地挖掘了云南诗人的写作特色。同时,她在《云南大学报》上开设 云南作家专刊 栏目,对云南的小说写作开展个案分析。
现在,对云南批评家的批评声是很多的,其中一股声音就是说云南的批评家不关注云南的创作,这对,也不对。没有那一个批评家是专门为那一个群体或地域做批评的,但一个地域的文学要想良好地发展起来,批评家和作家的良性互动是必要的,那么,蔡丽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这些研究,还未引起更多的重视,但涓涓细流,终会汇聚成海,形成对云南文学发展的良性因子。
希望在蔡丽,还有很多年轻批评家身上,看到云南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成长的喜人发展。
批评要去职业化而变为生活化
蔡丽周明全
现实主义就是敞开心胸去接受新的现象
周明全: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历?
蔡丽: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读本科,中国文学与广播电影电视专业(当年影视刚刚兴起,隶属中文,于是我们非师范专业的就变成了杂学。哈哈);年在西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年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2006 年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
周明全:在文学这个行当混迹了十多年,你是在这个行当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或者说受那些著作的影响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还是说你做文学批评是一路走来的教育惯性所为?
蔡丽:几方面的原因吧。关键是大学毕业时的选择。大学毕业不好找工作,尤其是我想到昆明来找工作,可坐在板凳上一想,我在昆明一个人都不认识,这没法找啊。想想办法吧,嗯,级别高一点吧,于是考研。同时受环境影响。我大三时候搬到了一个有一点屌的学霸宿舍,大家相处甚欢 首先有一个立志回家的要考郑大,另一个立志电影的 看上了 北影回来的余纪,然后我就跟着心动了,想想电影实习的时候摄像机扛得太累,当演员也缺乏镜头感,还是回到比较闷一点的位置吧 文学。选择文学自然受到授课老师的影响,那时候西师老师都各有特色。像虞吉老师,他给我们上完了整个欧洲和美国的电影史,虞老师是一个严谨而不乏诗意的老师,极有魅力,开讲前必抽一支烟,烟头一扔,张嘴说话,声音充满磁性,据说我们班有不少女生是目不转睛盯着他的。他的风格是海量信息插播精简花絮,上课时你总会心甘情愿地写酸笔头,他同时每周给我们业余配送两次观影。按电影史来放,听起来很不错的待遇。但是,太可怕了,我们要记镜头,曾经一部片子记过近两百个镜头,啊,疯掉。但是,它锻炼了我们的观察和思考能力,非常过瘾。上外国文学和现代诗歌的李怡老师,他现在在北师大诗歌研究中心。他有诗人的一面,讲课语调高亢、富有 ,作品分析课总是上得我们心潮起伏,同时,他是一个思维特别严谨的思考型学者,一般来说,他一节课就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的心思都在跟着他的推动迈步,这种上课方式我现在还用。还有王本朝老师,他是讲知识点的时候平铺直叙,一进入人物和作品分析就好像把酒喝开了一样,撸起袖子给我们津津有味的讲。还有我的导师董小玉,她是一个高挑个的有着长长独辫子的风度翩翩的女性,上课 四溢,你可以想象,那辫子一甩转过身去写黑板的魅力。大学的老师都是有特点的。而我在大学也正是那种喜欢有点特点,痴迷专业,其他乱七八糟的课程混六十分的类型,台上这些风采奕奕的身影已经潜移默化入我的心中。所以,我不跳舞了,我要搬寝室,考研去。
周明全:西师不错啊,这么多很牛的老师,那你为何都没受他们他的影响,做电影批评或者诗歌皮革研究,而是在博士时做起了左翼文学研究。其实,我一直很纳闷,不少博士的博士论 的是左翼文学研究,这是你们主动的选择,还是受导师的影响?这段历史值得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去研究吗?
蔡丽:现在左翼又火起来了。当年我准备做左翼文学向工农兵文学的转型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傻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现代主义盛嚣世上的时候,我那时一口气把各种现代概念的书爬了一遍,爬完了就不想干了。我这个人天生性情有点喜欢靠边站,我就想,博士论文,应该是自己学术训练的一个方式。那我要按照完善自我的方式来。硕士时候我做的是当代的一个作家的研究,博士我就想想做一段时期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这样就从作家作品论过渡到史论。有了这个方向之后,做哪一段呢,考察了我自己一下,最混乱最不清晰的就是40年代左右,好,那就这一段吧。这一段是所谓现代和当代的衔接点,后来,文学史的代际衔接的研究成为热点,那是后话。至于左翼的研究其实一直也不是很热门。但它总有令一个研究者心向往之的地方,就是人与政治、与党派、与文学之间非常复杂的关联。我们看到的文学史往往是表面,当你深入文学,你首先触及到人,再深入,触及政治。左翼总体文学成就不高,但涉及透彻了解新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现实问题,所以,很多研究者愿意深入。不是为了提高左翼的审美评价,而是认识文学本身的性质:中国现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它多大程度上是人的文学,是美的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
周明全:之前和不少做左翼的批评家聊过,他们的看法和你很相似,看来,看来是我低看了左翼文学的重要性。那请你谈谈左翼文学研究对你的启示,或者说对你此后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
蔡丽:我从中深刻体会到两件事,一,文学是人的文学。二,中国的文学,离不开社会背景。所以,老一辈提出知人阅世,我认为到今天也是有魅力的。另外,我的研究,可以从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跨度到文学史段的现象把握了。既有大局,又有细部,以后再加上理论,这是我今天在评价很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都一直受用的思维习惯。
周明全:你博士论文还牵涉一个左翼文学向工农兵文学转变的问题,这主要的是政治的需要,但这是否也意味着是文学的代际变化的一个结果?你如何看待代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蔡丽:代际研究,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十几二十年间,你已经找不到故乡。非常可怕。城头变幻大王旗啊。而且,代与代的问题不断变化,我做代际研究的时候,核心问题是政治主导下的文学转型,今天是络数字化时代,全球一体化时代。代际的转换在悄无声息间进行,很多西方的哲学家、传媒思想家已经敏锐到时代的巨大变化而努力做出应对。我们也应该有所反映,什么现实主义,就是你必须时候放弃你习惯的眼光和思维,敞开心胸去接受新的现象,然后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思考这些现象。比如你做 80后 文学,这已经是 0岁的全络化生存的一代,打的都是用打车软件,我们真正了解他们吗 需要把他们推出来。让我们睁大眼睛认识当下。
当下的文学教育重知识少实践
周明全:从苏州大学毕业来到云南大学教书,已经快十年了吧,这几年,我看你也很少写文章,是觉得云南没有好的批评环境,还是身为女人,将更多的时间用在照顾家庭上了?
蔡丽:我是本硕博一直读,博士期间生的孩子,怀孕一个地方,生一个地方,带一个地方,现在想来都后怕,完了后就累得不行了。很多东西都来不及消化,包括知识,包括生活。我需要重新审视。所以,这些年,研究做的零零碎碎,却真正清楚了我和文学的那点关系。当然,来到云南,是个陌生地,我以前的平台也就不在了。这些年的学术空气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自己又是一个喜欢靠边站的人,相当寡淡,对名和利都没有什么奢求,所以就姑且零零碎碎了。研究也是一辈子的事,总得和其他的生活进行协调,那就慢慢来吧。
周明全:给我的感觉,你博士毕业后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相对很零散,做过鲁迅研究,做过小说批评,这几天又转向诗歌研究,这是一直未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蔡丽:鲁迅研究是和一个老师合作做一本鲁迅研究的书,答应了就全面梳理了鲁迅,当然鲁迅也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个作家。这事完成了就没再深入。小说批评一直都做,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摆脱不了小说的诱惑。其实有一个转向是从博士论文的现代文学史现象研究转向云南文学的关注。云南的小说,诗歌,一直都关注,也一直在做评论。有一段时间感到当下的中国小说读得我很厌倦,大概是作家们习惯电脑写作动作很快,出产也非常快而丰富,在质上始终有些令我失望,便转向更 心灵的东西。诗歌当然也是江湖,诗人之间,彼此更加看不起,但是,不少诗人面对文字的舞台,他还是习惯淋漓尽致地表现,你总能遇见打动你的,直击生命、自由、情感、人性的诗行。
周明全:那你近年转入云南诗歌研究,应该是和你对诗歌的理解有关吧!
蔡丽:是的。从云南诗歌我找到一些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做研究其实很没有抱负理想,纳博科夫写过一部小说叫《微暗的火光》,文学对我而言,就是茫茫黑夜中的那个微暗的火光。我从它认识心灵、人性、美,反过来观察我自身,确定我自身。所以我的研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选择触动我心灵的那点东西。我不知道今天的活跃的批评家有没有按照自己心灵的需要来做研究的?我也不管了。对我而言,打在我心坎上某处地方的,才是我有兴趣下笔的。
周明全:作为老师,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教育?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应该如何做,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蔡丽:当下的文学教育重知识少实践,学生的作品阅读兴趣不高,几乎是老师逼着读。经典意识不强,还有就是老师的时尚步伐跟不上学生。我的做法是强化阅读,讨论和抽问。写作课会要求学生大量的写。
边疆文学批评是属于地域的边缘上
周明全:作为做文学批评的人,你如很看待云南近几十年的文学发展的?
蔡丽:云南文学在八十年代真正拥有了自己的作家梯队,近几年获鲁奖的也不少。诗歌、小说的有名的作家几乎个个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一点非常可贵。它意味着云南文学从整体的高原地域风格上保持丰富和多元的个性面向。诗歌的成就我觉得目前是要高于小说一些,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
周明全:对云南文学的整体认识,我和你持相似的观点。我这些年和外地的批评家聊天,当我谈起云南的一些批评家时,绝大多数都不认识,在他们眼中,云南是没有批评家的,你如何看待云南的批评圈?你认为,云南的批评家不被主流认可,是因为地域缘故还是说云南的批评家的确做得不够好?
蔡丽: 我认为这首先不是批评家的问题,因为当下云南很多年轻的批评家都有在外省名校跟随名师求学的经历。在知识结构上、思想思维上都不弱于外省。关键在于平台。比如你推出的 80后 批评家,除了你自己,其他都是投身名门,在导师的带动和举荐下进入研究的热场,北京、上海、南京,基本上三分天下嘛。我以前在苏州的时候发《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的稿子都可以,现在反而不行。我想,这肯定不是我现在写文章糟糕了,而是这是一个人的圈子,我没有去找人,近十年不出去开会,当然就在圈外了。应该说,我接触过海外的青年批评圈,国际汉学的批评圈,也有北京、上海、南京的批评圈,反过来看云南本地的批评圈,高校的力量很隐没,但力量不容忽视,民间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很有个性,接地气,有感觉,我认为也是挺好的。是否在外省有影响名气大就代表学问高,在今天的整个学术机制下,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周明全:在这点上,我和你持相反的观点,在当下这个信息化、络化时代,想埋没一个有真正才情的批评家是很难的。圈子化固然是批评界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大问题,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才情,文章写得好,跟在什么地域没太大关系。从诗歌的角度看,雷平阳身处云南,早年还在更偏远的昭通,但他就是凭借自己的才情和对诗歌的透彻理解和创造实践而被外界认识、认可的。批评虽然和创作有些差别,但本质上一样的。我看前久你们在讨论,边疆地区的批评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讨论的结果是什么?你们认为边疆地区的批评家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蔡丽:这也是针对云南的中青年批评家缺乏发声平台的问题而讨论的。我们有时候眼看着明星去崇拜,却忘记了身边真正关心你了解你对你有意义的人。当我们让佤族、拉祜族、彝族、苗族等民族丢弃它们的民族习惯而上、用、讲普通话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最珍贵的个性和历史。我想,学术也一样。都跟着潮流走,会议走,大师走,边疆的拼命学习主流城市的。那会是怎样的世界?说的透一点,这是一个话语霸权下的利益问题,作为一个地方和一个个人,怎么度量,是需要冷静思索的。
周明全:那依据你的观点,你认为,像云南这样的地方,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批评家队伍?
蔡丽:扶持。
周明全:呵呵。看来我们文化人还是太天真了。
70后 一代太西化
周明全:《边疆文学 文艺评论》从2015年起增设了 青年批评家 栏目,请我主持,其主要想法就是推出更多优秀的青年批评家。 80后 批评家这两年,在中国作协、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批评家文丛 等刊物和出版的集中推介下,已经形成了集团优势,而 70后 批评家虽然涌现出谢有顺、霍俊明、梁鸿、张丽军、房伟、李云雷、张定浩等一大批优秀的批评家,但似乎在文坛没有形成一种整体性的优势,无法获得相对集中的命名,整体感觉是被遮蔽的。作为 70后 批评家中最为优秀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待 70后 批评家被遮蔽这一现象的?作为其中一员,你觉得这个群体的整体实力如何?
蔡丽:其实,遮蔽这个词你要怎么看。一方面,批评也好,学术也好,都已经是人的圈子,在庞大的竞争下,自然形成某些群体的话语权和更大多数人的边位形态。从这方面看, 70后 的确是被遮蔽的,你想,全国有多少所高校, 70后 有多少具有博士研究生及以上文凭。他们都在默默辛苦地工作。谢有顺、霍俊明、梁鸿等是 70后 已经卓有成果的一批人。但另一方面来说,严肃文学在今天又有多少人关注,一个批评家和学者探讨的问题又有多少人关注,有多少人的书只是写给自己看,所以,不仅是 70后 被遮蔽,而是整个严肃文学的写作、研究、和批评,都处在一个层层边缘和遮蔽状态下,就那么大的台子,总有人被挤下去,这也是常态。
周明全:你说的不无道理。用陈思和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无名状态。但其实,无名状态也没什么不好。陈思和在和金理的对话《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曾说过, 70后 80后 作家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导致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批判,由这些表达出来的经验就得不到批评家的呼应,但这两年, 80后 作家和 80后 批评家同步成长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而 70后 作家才是真正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没能和同代批评家相互呼应,不少人以为这是 70后 一代作家和批评家被遮蔽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蔡丽:相互呼应这个问题,陈老师自有高见。我想关键的还在于我们这一代太西化和理论化了,与创作直接脱节。这是一代人的学术潮流问题。整个90年代以来,我们似乎都在拼命地拔高理论,以前我在南大的师兄,他自从读南大的博士后,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喜欢的创作,因为导师不允许他再搞创作。我们一本一本地啃理论书,比很多美国人更了解他们的批评家,却极少有人,真的极少去和作家打成一片的。我们甚至排斥做当下的批评,那是学术规范,进门的时候导师就已经讲了的。加上大多数搞文学研究的其实都是乖学生,特别懂事特别规矩特别上进,并不见得是文艺青年,真正的文学的心性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更不要说生活阅历了。而当下的作家们恰恰是以阅历在写作,以个性表现和人性的深度挖掘为突出特征,所以, 70后 批评家几乎自然而然和作家划清了界线,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但批评家和作家打得太火热也不行,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双方合谋下的话语权的双赢,文学就成了 裸的商业运作。
做文学评论要有充分的准备
周明全:听很多高校的老师说,要评职称,就必须申报课题,而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故纸堆里,自然就对当下的文学关注少了,另外,高校考核体系中,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而对当代文学缺乏研究热情,这也是当下批评为何无法深入研究当下文学的一个原因吧?作为高校教师,你如何看待课题对文学批评的利与弊?
蔡丽:以前我们做当下文学的研究,那都是不务正业。课题,很多老师都非常头疼的东西,所有的课题都是上面出好了题目让我们来选报的,它其实属于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对思想的管理问题。有了它,相当于批评的主流话语是早就设定好的。不报也不行,像云大,没有国家级课题,基本就别想评教授了。不报课题就没有研究经费,报上了课题你就整天琢磨怎么报账 帐奇难报。这是勒脖子的一根绳。至于中间的猫腻就实在懒得说啦。
周明全:纸媒日益边缘化,学术刊物、评论刊物更甚?如何让批评重新建立与这片土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血肉关联。
蔡丽:大量的学术刊物、批评刊物最终都沦为同人刊物。同人,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络上就有同人小说。要让批评重建与大地和现实之间的关联,我想批评要去职业化而变为生活化。批评家做批评最好是做给自己的,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批评个性。否则,有太多的话语,只是从某个西方思想家那儿贩过来,经由一些会议和文章和媒体,变成一定时期的批评风向,利益在这过程中彰显,这太可怕了。批评要去观察创作,深入地了解活生生的作家,解读他。批评要有是非观,宽容现实,思考生活的积极意义和人的需要。我认为这些都是今天的批评冲破同人圈子所必需的。
周明全: 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蔡丽:充分的文学储备,你心里得有一张地图。文学直觉要好,没有感觉怎么下笔。最后,真诚。
周明全:谢谢!
淮安治疗白癜风好的医院小儿厌食颗粒
老年风湿骨痛怎么治疗
下一篇:我第一次在人海中见到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