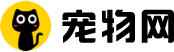自强圪针和我同岁
更新时间:2020-09-14 15:51:28
圪针和我同岁。
在我的记忆里,圪针似乎智力有些问题。尽管他比村子里的海娃和老晕聪明得多,懂得人情世故,但他始终比不上我们的伶俐通透。
圪针的脸上,始终挂着笑。那笑,真诚,质朴,纯净,憨厚,阳光般轻柔,以至于我离家这么多年,他的笑,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
圪针很像他父亲。低矮的个子,上牙凸出嘴外,使嘴唇用尽气力,也无法完成覆盖牙齿的基本任务,就像他家院内的那棵老槐树,夸张地向外伸露着畸形的躯干。
圪针和他爹,形影不离。村人说,父子俩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两只屎壳郎。这话带着一种调侃和揶揄,但他们父子俩听到,不仅不生气,还相互看看对方,乐呵呵地笑。
圪针也像他爹一样,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端着海碗,站在家门口的大街上,逢人便问你吃饭没有或者你下地啊之类的话。这些话,在村人眼里,无关疼痒,甚至有些人因为心情不好,还假装没有听见,不理他们。
圪针的父亲叫老观。老家很多人的名字,只能叫出音,而无法用字去写。直到如今我也弄不清楚,老观的“观”,是不是这个字,姑且随了电脑,权当如此。
老来自研讨会的资料显示观经年累月重负,脊背已经变形。他走路时,夜叉一样撇拉着双腿,整天破衣烂衫,胡子拉茬,上面粘着饭咯巴,脸上皱纹的沟槽里,塞满着泥土。但他诙谐幽默,乐观豁达,走在村子里,人们都喜欢和他轻松地打着招呼,甚至插科打诨,与他逗乐。圪针这时候就扛着撅铲或者锄头,走在他爹身后,咧着大嘴,但不敢笑出声。
圪针不敢笑出声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在开他爹的玩笑,骂的是他祖宗,笑出声怕别人笑话,可能还怕他爹骂或打他,所以总是尽量忍着。但人多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玩笑开得没边没沿,老观一口难抵众嘴,总是招架不住,只有吃亏的份。看着老观尴尬的模样,大家都被逗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圪针也就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老观这时就会扭过头,瞪大双眼,笑着骂圪针:你他娘的也敢笑你老子。
天长日久,圪针和老观父子,成了人们开心的原料。他们走到哪里,哪的笑声就会不绝于耳。村人开心的笑,一阵阵地飘在空中,滑入心里,温暖而轻柔。
圪针姊妹四个,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圪针听话,老观下地,总喜欢带着他。老观一辈子与世无争,与人为善,他带着圪针,经常在田间地垄做一些别人认为很傻的善事。比如,修路搭桥这种生产队的官活,他们父子俩却好管闲事,见着就修,也没有要过报酬。
老观经常会在大热天的晌午,收工回家的时候,让圪针扛着农具前边先走,自己在地里找块相中的大石头,气喘吁吁扛着回家。
那时候,老家的村子里,全是草房。老观有个心愿,他想为儿子盖起一座瓦房。他始终坚信,到他老了,干不动的时候,他的这个愿望就会实现,他年轻时背回来的石头,足够两个儿子盖房子用,只要盖起瓦房,两个儿子就能娶上媳妇,就能过上好日子。他总是这样默默地想着,这种简单的想法,让他锲而不舍地将一块块的大石头坚持往家背。他牛皮般粗糙的脊梁上,汗流如油。
老观把背回来的石头,整整齐齐堆在院子里,或者端端正正放在家门口的墙边,一字排开,让人先坐。
收获的季节,老观和圪针从地里回村,兜里装着野枣之类的山果子,散给我们。他们还时常从村南坡干完活,抓野鸟回来给我们这些小孩子玩,偶尔还能看到圪针抓回一只可爱的松鼠,高兴得我们大声惊叫着,呼唤伙伴一起来玩。
那天,圪针给我们带回来一只刺猬。那只刺猬见了人,缩成圆球般的一团,浑身的尖刺犹如钢针,密密地保护着它的周身,弄得我和小伙伴不知所措,只能拿树棍去轻轻地拨拉。玩到太阳落山,我们不知但也不算便宜。建议大家有元宝的话都是可以多够买几次的道将刺猬如何处理,我将刺猬带回了家。晚上,那家伙不知怎么钻进了父亲的被窝,父亲将我臭骂一顿,将那只刺猬放进黑暗的野外。
圪针家的门口,摆着一副石臼。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磨,粉碎粮食,全靠这原始而笨拙的石臼。这样的石具,由一把带木柄的圆石锤和一个圆柱体的大石凹底座组成。这副石臼,是老观掏两斗玉米让一个外地的石匠打造的,放在家门口,免费让村里人使用。
有月亮的傍晚,村里人就聚集在圪针家门口,轮着捣粮食。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母亲坐在圪针家门口捣玉米。母亲那晚心情很好,她一边捣着玉米,一边笑着问我,你仔细看看,月亮里藏着什么。我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银色的月宫,隐约飘浮着一个清幽的影子。我问母亲是什么。母亲说,月亮里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叫嫦娥,因为犯错,受到天庭惩罚,所以她也在月亮里捣粮食。我问母亲,嫦娥有多美。母亲说,嫦娥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自此以后,我喜欢上了这个故事,喜欢上了那个住在月亮里的嫦娥。
总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我坐在圪针家门口,听着村子里捣粮食的咚咚声,静静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那沉闷而富有节奏的声响,仿佛是从遥远的月宫里飘出来的曼妙韵律。沉浸在这样的幻想里,幼小的我,就那样做着美丽的飞天梦。
十年后,当我真的成了一名天之娇子,穿云破雾飞翔在深邃而广袤的天空,我还会想起当年坐在圪针家门口的天真模样。尤其在夏季的夜航期间,那么近距离地贴近月亮,徜徉在她的光辉之中,我会时常想起母亲当年给我讲的那个神奇而美丽的传说,心中不免轻轻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感伤。
圪针一家人都很善良,而且十分和睦。在我的印象中,他家从来没有吵过架。这让当时经常品尝着父母打闹苦痛的我,十分的羡慕。
但我听母亲说,圪针家曾经在早年,和对门的老三家吵过一架。而且,那次吵架,让圪针一家人从此不敢再和村人争执。
那时候,我和圪针都还没有出生。老三的父亲是生产队长,在村里很霸道,整天瞪着一双凶神恶煞的眼睛,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村里人对他既恨又怕。圪针外婆住他家隔壁,因为邻里纠纷,老三的母亲指桑骂槐,这让圪针娘很生气。
之后的有天早上,老三的父亲领着生产队社员从地里干活回来,又听到圪针娘和老三娘在争吵。他暴跳如雷,准备跳下台阶,去打圪针娘,却一头栽倒在地上。
圪针娘见此情景,吓得扭头钻进了家门。
一街两行看热闹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人们沉默良久,才清醒过来,吆喝着跑去救人,但最终没能将老三爹救活。
现在看来,老三爹的死,应该是急火攻心,导致脑溢血或者心肌梗塞而丧命。但在当时,人们都以为,老三爹是被圪针娘气死的。只是村里人都憎恨老三爹娘,没人帮他家说话。况且在当初,村里发生的事情,是以道德和良心去判别是非,很少经官动府。所以,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尽管两家以后为此结下仇怨,而且持续多年,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圪针一家人在村人中的良好形象。
圪针没有上过学,所以不识字,尽管他十分想读书。
父亲领我第一天去上学的那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薄薄的晨雾笼罩着大地,很多小鸟栖息在高高的枝头,热热闹闹地盘旋跳跃,啁啾鸣叫。
走在村口,我看到圪针正挑着两罐尿,一摇一晃往地里走。我和他那年都七岁,他吃力地走在早晨雾色苍茫的太阳下,背影映着蜿蜒起伏的山路,孱弱而单薄。
之后的日子里,圪针每次见我,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但是,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因为不能和我们一样去上学而耿耿于怀。他脸上的笑,多了一份苦涩和痛楚。他躲着不见我们,偶尔他从地里回村,在放学的路上碰到我,总是轻轻笑一下,然后低着头或者迈过脸,不和我们说话。
沧桑的岁月,磨难的生活,锻造了圪针的承受和忍耐能力。他开始渐渐成熟,长成一个强壮魁梧的年轻人。
圪针依然和他爹老观形影不离,春种秋收,继续着周而复始的田间劳作。
没有人给圪针上门提亲。这是一个偏僻而闭塞的小村,年轻人说媳妇本来就难,何况他爹还没有将盖房所用的石头背够,他们兄弟期盼的瓦房,还始终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老观却在一天天衰老。
冬天的一个早晨,老观在地边扛起一块石头,他感到一阵头晕,踉跄着身子,倒在了地上。
老观鼻子在流血。殷红的鲜血,滴在他破旧的黑棉袄上,滴在黄黄的泥土里,而且那血,滴得越来越快。
老观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感到了死亡,他看到一个幽暗的影子,正在轻轻向他走来。他知道,那个影子,是阎王派来的鬼。所以,他骂了一声:真他娘的,见鬼了。
老观吃力地将身体扭正,躺平,躺在太阳下。太阳有些晃眼,风从他耳边轻轻吹过,他感觉有点冷。他静静望着澄澈明亮天空,长叹了一口气。
他还没能将瓦房给儿子盖起来,他不甘心就这样倒下。
圪针见老观在不断流血,跑到远处,拣了一团废纸,又快速跑回他爹身边,跪在地上,把纸捂在老观鼻子上。
老观望着圪针,他感到愧对儿子。他强装镇静,对跪在他身边的圪针说,他娘的,石头我是背不动了,你自己背吧,把瓦房盖起来。
那天,老观被人从地里抬回家,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老观死后,圪针不仅像他爹那样背起了石头,而且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圪针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娘也浑身病,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弟弟小,还在上学。
圪针脸上没了微笑,他开始沉默寡言。村里没有人愿意聆听他内心的苦,而他也不想和别人枉费口舌。所以,圪针学会了吸烟。
烟成了圪针唯一的朋友,成了他缓解疲劳的唯一途径。他抽不起买的烟,只抽自家地里种的烟叶。
我当兵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很多人来为我送别,包括圪针。
当时,我的心正被理想实现的喜悦和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情绪所淹没,根本无暇顾及他。
圪针坐在我家院里的一个角落,默默抽着我递给他的香烟,一声不吭坐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所有的人全部离去。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特别的困,也觉得没有和他交流的必要,随便敷衍了他几句,就撵着他回家。
他缓慢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脸上挂着谦卑的笑。
他说,你走吧,您伯您娘我会帮你照应的。
那一瞬间,我很感动,我甚至产生一种想拥抱他的念头。
至今,我觉得在老家整个村子的所有人里,圪针给予我父母的帮助,最直接,最慰贴,最温暖。他对我父母的给予和付出,是生命本源的良善,从不要求回报。
当兵之后,我很多年没有再见过圪针。
我从部队飞院毕业,分到郑州。我回老家,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将父亲和母亲接进县城。
这个决定,是我两个多月前看了父亲写给我的家信中描述圪针在冰天雪地的早晨天天给他们挑水的情景时做出的。
老家村里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水井挑。村里的水井离我们家虽然很近,但需要负重爬上一个四十五度的高坡,而且水井没有辘轳,遇着雨雪天,泥泞不堪,容易滑倒,甚至还有掉进水井的危险。在我走的那段时间,圪针看我父母年迈,总是在雨雪天气,先给我们家挑完水,再干他们家的活。
我让父母在县城住了三年。
我结婚之后,又将父母接到郑州身边,生活了将近六年。
这近十年间,我甚至也像父亲当年那样,憎恨故乡,憎恨那片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悲凉和薄情,加之父母不在老家,我再没有回过那个小村,直到父母再次回到小村生活。
在我开车送父母回村的路上,内心千头万绪,汹涌澎湃。很多过往的曾经被尘封在心底的旧情旧债,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地,重新活灵活现地浮现在脑海。
车到村外,已经傍晚,母亲执意要走路回村,犹如她在郑州执意要回老家一样。
母亲在村口,遇见了圪针娘。圪针娘五大三粗黑如煤炭,根本不像个病人。她紧紧拉着我母亲的手,泣不成声。
我将车停在门口,家门前,荒草疯长得比人还高,太阳橘色的余辉,斜斜地从村西的树下照进来,整个村子犹如一条黑暗的时光隧道,只有柔和的阳光穿行其中,照亮于此。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心突然疼了一下。父亲看起来也很伤感,他下了车,默默从邻居家借了把铁铲,清理着门前的荒草和杂物。
我到村口接母亲。圪针娘还和母亲在说话,只是不再掉眼泪,脸上有了笑。
这时候,圪针挑着麦秸走进村。他头发蓬乱,满脸污垢,整张脸几乎被胡须所覆盖,俨然一个乞丐模样。他见到我,挤出一个微笑,说你回来了。我赶紧走过去,给他掏烟。他把箩头放在地上,拄着扁担,不知所措地抽着烟,听他娘和我母亲说话。说话之间,暮色四合,我和母亲回了家。
后来,我经常回去,只是没有再见过圪针。父亲去世后,我又将母亲接来郑州,住了两年。
母亲在郑州的这两年,我的心非常塌实。一家人团聚,心不再四分五裂。可是,母亲怕自己年纪大,老在外面,非要回老家不可。我想想也是,母亲已经八十四岁高龄,我必须让母亲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因此,我再次送她老人家回去。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次回去,圪针娘已经不在了人世。
圪针娘是在我送母亲回村子的前一天去世的。据说,她患了癌症,而医院误认为是结石,开了刀,又合上。回家不到半年就死了。村里因为死了人,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我将母亲安顿好,晚上来到圪针家,为圪针娘上了一炷香。
圪针弟弟本来在郑州做土产生意,去郑州多年,我根本不知道。在他娘得重病后,回了老家。圪针的两个姐姐也在。原本准备盖瓦房积攒的钱,为给母亲治病,花掉了。所以,他们仍然住在原来低矮而破旧的房子里,瓦房始终没能盖起来。而且,即使瓦房盖了起来,与村子里相继拔地而起的楼房,也根本无法对比。
圪针一直没有娶上老婆。
圪针还像他爹老观那样,一直往家背石头,而新房却永远也盖不起来。
圪针也许一辈子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之中。
圪针别无选择。
2008年7月16日
共 51 1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圪针很像他父亲老观。低矮的个子,上牙凸出嘴外,使嘴唇用尽气力,也无法完成覆盖牙齿的基本任务,就像他家院内的那棵老槐树,夸张地向外伸露着畸形的躯干。圪针和他爹,形影不离。村人说,父子俩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两只屎壳郎。于是,圪针和老观父子,在村里,人们都喜欢和他轻松地打着招呼,甚至插科打诨,与他逗乐。圪针没有上过学,所以不识字,尽管他十分想读书,圪针长大后,没有人给他上门提亲。老观每天要背块大石头回家,想拿来给两个儿子盖房子用,只要盖起瓦房,两个儿子就能娶上媳妇,就能过上好日子。可圪针老爸终于没等来儿子娶媳妇的那天,冬天的一个早晨,老观在地边扛起一块石头,他感到一阵头晕,踉跄着身子,倒在了地上。那天,老观被人从地里抬回家,不到两个月,就死了。老观死后,圪针不仅像他爹那样背起了石头,而且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从此,圪针脸上没了微笑,他开始沉默寡言。多少年之后,圪针一直没有娶上老婆,像他爹老观那样,一直往家背石头,而新房却永远也盖不起来,也许圪针将一辈子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之中吧?看了这篇小说,心里觉得无比的心酸。圪针,这个善良勤奋的人,为什么命运却如此悲惨?他的愿望好简单,只是为了能盖上一间房子,能娶上一个知冷知热的媳妇,但上天偏偏没有满足他小小的要求。此篇小说,人物形象描写非常完美,刻画十分生动,栩栩如生,如就站在读者面前似的。很佩服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很精美的小说语言,推荐欣赏!【:一盏茶心】【江山部精品推荐01 0 0 8】
1楼文友:201 -0 -01 20:04:18 感谢赐稿天涯,问好老师,辛苦了!
嘴角溃烂
小孩子不爱吃饭
牛奶蛋白过敏能自愈吗